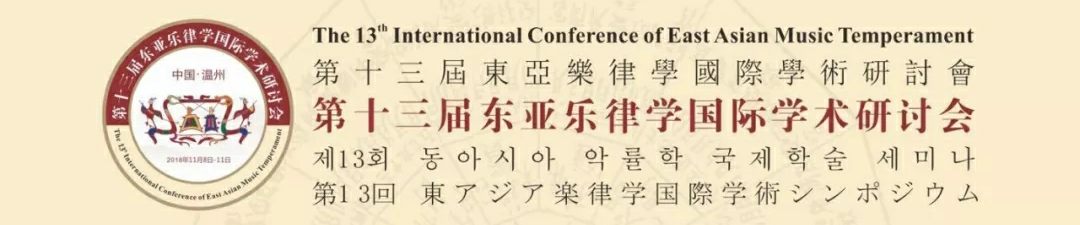

10号上午第二阶段的研讨中,安徽师范大学李建栋副教授、韩山师范学院周天星副教授、山东艺术学院朱仲毅博士依次发言,广州大学何燕姗博士后和华南师范大学杨石磊博士后联合提交论文。
【第六单元】

李建栋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《<类筝治要>中部分未标定节拍点位唐乐系统曲的节拍划分》。解译唐传古谱时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是节拍划分,若节拍划分不明,解译的曲谱必然产生旋律怪异、起承舛忤等诸多不谐,故厘清节拍划分思路、总结划分规律是解译唐谱的必要环节。
对此,发言者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:(一)问题的源起及学界研究现状。关于唐传古谱的节拍划分,学界的讨论已有80年。对国内唐传古谱节拍划分的讨论主要集中于《敦煌琵琶谱》,对国外唐传古谱节拍划分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日传唐谱《仁智要录》《三五要录》《五弦谱》《怀竹谱》等。关于《敦煌琵琶谱》的节拍划分,盖有八类十种观点。(二)考察结果。唐传筝谱《仁智要录》《类筝治要》有两种节拍标定体系,一为右标点的小拍子体系,一为小标点的只拍子体系。连词操、大图操、中图操、小图操、仲大图操五种节拍标定方式属小拍子体系,曳累操、中弦操、喘吠操、仲吠操、仲小曲操五种节拍标定方式属只拍子体系。小拍子诸操演奏速度整体较快,属急管繁弦型风格;只拍子诸操演奏速度整体较慢,属轻拢慢捻型风格。两体十操的本质区别不在节拍标定方式,而在乐曲演奏之缓急、轻重等风格。(三)问题的解决。对无任何下标点、右标点的曲谱进行节拍标定,分为一般解决方案与特殊解决方案。一般解决方案是将《仁智要录》与《类筝治要》进行对校。而特殊解决方案是解译者可扩大查阅范围,找出曲子的类型或结构属性,在此基础上,通过考察该曲单个谱字所用演奏时长判断再进行解译。

周天星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《唐代定调管色形制之研究》。以管乐器作为定调定弦之实践在我国有很久的历史,及至隋唐,以笛定调已成为一种机制。具体方法是,琵琶、筝上某调音阶对应笛上某调音阶。这种记载反映出,唐代笛类乐器具有旋宫转调之功能,故而其形制应为均孔形式。发言者认为,要了解唐时雅乐、胡乐以及俗乐乐调的问题,应从定调管色乐器入手,故以主要定调笛类乐器为研究物件,以日传唐谱《三五要录》中以笛定调的方法和相关历史记载为依据,来确定唐代管色定调形制的基本面貌。进而指出,唐代音乐实践主要存在三种定调笛制,即“雅乐”黄钟笛、“胡乐”太簇笛以及“清乐”林钟笛。三种笛形制为类“均孔笛”,可以实现“七宫”转调之需要。

朱仲毅博士的发言题目为《“变宫在宫后,变徵在徵后”解析》。所谓“变宫在宫后,变徵在徵后”是明末以降笛乐转调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表象,清代学者对此有详略不同的讨论,这在毛奇龄的著作中格外突出。以毛奇龄《竟山乐录》中的两段材料为例,呈现“变宫在宫后,变徵在徵后”的七声音阶,相较于传统七声,这样的排列形式自然有悖于传统乐律学理论而令人费解,但却得到了当时学者们的认可。发言者首先对有关“工尺七调”的十五部文献作了梳理和分析,结果显示,毛奇龄所处的清初时期,对笛上工尺七调描述较为详细、准确的当属《律吕正义》中的记载。其次将《竟山乐录》与《律吕正义》所描述“正宫调”结构对比,分析其逻辑内涵,呈现这一现象在当时具有普遍性。最后分析了这一现象的产生与笛上翻调之间的关系。进而得出结论,这一现象是明末以来乐人笛上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表象,亦或是一种指示不用两音所在的笛上口诀。

何弘珊、杨石磊二位共同提交的论文题目是《“三分损益法”始发黄钟律的生成问题探究》。“三分损益法”在中国古代律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,关于其起源和算律方法等问题,学界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,但对于其始发律是如何生成的,为何要把“三”作为算律参数进行计算等问题则鲜有人关注。作者结合相关文献,对“三分损益法”始发律的生成问题进行了考察,认为“三分损益法”的始发黄钟律不是任意设定的,它是从“中声”当中按照“纪之以三”的原则生成出来的。由于“中声”有相应的固定音高,所以按照“三分损益法”生成的十二个律音在实践运用中也对应着固定音高,这样才能在调律实践中实现乐器音高标准的统一性。“中声”作为始发律的母体,在古代律学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,它相当于先秦哲学中的“阴阳之道”。在先秦哲学中,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,而在“三分损益法”中,“中声”就是十二个律音的母体,始发黄钟律就是“中声”按照共振原理被“纪之以三”而生成的,而其他的十一个律音,同样是按照这个原则依次生成的。由于“纪之以三”的原则贯穿于算律方法的始终,并且其基础是经验层面的共振现象,因此“三分损益法”应该是一种古老的、相对比较粗略的算律方法。
